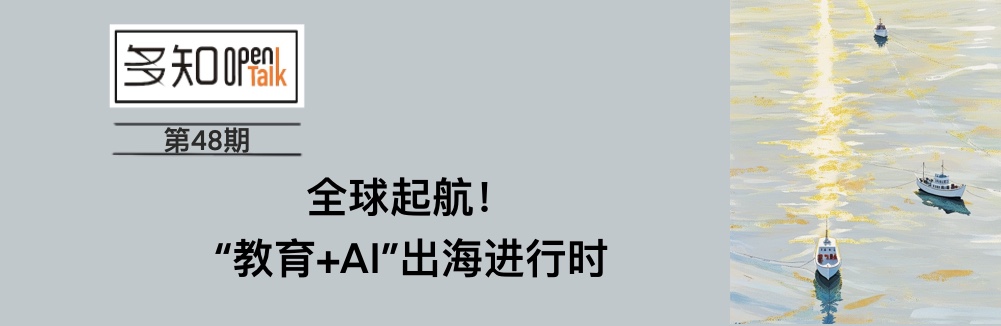当一条蛇出现在课堂
来源|多知网
作者|徐晶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周四下午五点半。西安某小学。三年级二班。自然科学课。
在全班孩子的注视下,粽子老师打开饲养箱,一条30厘米长的红棕色小蛇缓缓探出脑袋,继而不断蠕动,攀在他的胳膊上。
“啊!”全班孩子瞪大了眼睛,齐声惊呼,声音里透着害怕、惊讶及新奇。
“我们害怕蛇,这是正常的,蛇也害怕我们。但不要一上来就认为它是邪恶阴毒的象征,就要伤害它。蛇其实是很温顺的,很少主动伤人。这条小蛇是玉米蛇,它是无毒的,我们可以这样轻轻托住、观察它……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慢慢摸一下它。”在粽子老师的引导下,几分钟的讲解后,一个大胆的孩子上前近距离接触了蛇。随后,更多的孩子迈出了第一步。
课后,有孩子跑过来说:“粽子老师,小动物很有意思,我长大了也想成为动物学家。”
李宗瑾听后心绪复杂,但他一直记得,孩子的眼睛里有星星在闪烁。
(注:李宗瑾团队的一名老师在进行爬行动物课程课堂演示)
粽子老师叫“李宗瑾”,陕西昆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负责人,一个痴迷昆虫多年的爱好者。这是他正式成为自然科学老师的第1100多天。
从票友成为专家,继而带着团队走进校园、走上自然科普之路,这是一个年轻人兜兜转转、追寻最初的梦想的故事。
01
作为昆虫爱好者的那些年
李宗瑾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素描大蚕蛾,朋友圈里发的几乎都是和动植物科普相关的内容——他对自然生物的热爱显而易见。
这份热爱要追溯到小学。那时,校门口但凡有卖蚕宝宝、小鸡、小螃蟹的,他都买回来“凭着感觉养”,养死小动物的概率很高。妈妈只好心一横,不允许他再养小动物。
于是,李宗瑾转而开始关注昆虫,捉不同的小虫,放在铁铅笔盒里,悄悄带回家养。这算是他正式了解昆虫的开端。那时的他,还远不知道这份兴趣使然会贯穿他此后的工作与生活。
偷偷摸摸地养,遮遮掩掩地藏,认认真真地学,这是一个爱好不被大众理解的孩子在成长期对热爱的另一种坚持。
等到大学填报志愿时,在父母的建议下,选择主修就业前景更好的地理信息系统。他唯一的倔强是报考了一所农林类的大学,并在大学辅修昆虫专业。
(注:昆虫标本)
从大二起,李宗瑾开始制作标本,每年要做上几百份。由于标本做得精美,也打开一定知名度,他做的标本,一部分捐献给当地的标本馆,也供应给学校的特色商店。后来,他甚至做起了蝴蝶特种养殖,供应给云南景区及婚庆公司。
02
“看见孩子们的眼睛里有星星”
说起来,李宗瑾的人生轨迹被拉回到进校做自然科普的轨道上,是在2019年的夏天。凭借着专业,当时,林业口的校友邀请他给一所小学做自然科学的科普讲座。
“给学生上课时的感觉非常好。尤其是在问答环节,孩子们说自己平常看到什么不认识。然后我叭叭叭就给他们这么一讲,孩子们就用崇敬的小眼神看着我,他们的眼睛里有星星,那一刻我很有成就感。”
讲座的效果很好。于是,校方直接联系到李宗瑾,希望引进相关的自然科普课程。
随后,李宗瑾也以这样的方式走进其它学校。截至目前,李宗瑾团队累计走进了11所学校,其中长期合作的学校有三所。其中,有的作为学校特色课程引进,也有作为课后服务课程引进。
在课程内容上,由于昆虫学属于生物学的细分子领域,通常是研究生阶段才开设这门专业。因此,团队需要把专业知识内容不断降维,先给学生搭一个生物界的基础框架,其次讲解如何科学地观察动植物。此外,还有一类课程是与科研相关,比如带学生做生物种多样性调查,记录一个地区的生态变化。
(注:李宗瑾带着孩子们在户外识别常见昆虫)
举例来说,设计第一节课程的体系,通常先让孩子了解什么是软体动物,什么是环节动物,它的识别特征是什么。
其次讲解如何观察它们。比如植物,需要从根、茎、花、叶、果、实六个组成部分观察。观察昆虫就从口器、触角、目、翅、足观察分类特征。
第三,加入一些动手环节,比如带着孩子去做标本。
(注:团队另一名老师带着孩子们做蝴蝶标本)
最后是课程所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也尝试着让孩子自己去做校园内的动植物科普讲解。
可以看到,与一般的校内自然课不同的是,李宗瑾团队会加入实践环节,同时会带标本或活体作为演示的辅助教具进课堂。每一节课讲的不同的生物和不同的生物内容的时候,会配合着活体和标本让孩子近距离观察。
(注:“昆虫-自然界的主人”课程)
在活体动物的安全性上,团队通常买来大量的宠物蜥蜴、宠物蛇、宠物蜘蛛等的幼虫进行喂养,熟悉各类小生物的秉性后,挑出其中较为温顺的再带入课堂展示。
(注:团队喂养的小蜥蜴)
而喂养这些小动物,也比较简单,通常一周喂一次。李宗瑾回忆了一个细节:“2020年初疫情的时候,我西安的家里养了一些小动物,而我们公司是在杨陵,我当时在杨陵封闭几个月。在三个半月的疫情封闭期过后,我回西安接它们。它们都活着,也就相当于它们不吃不喝自己能扛三个月。”
(注:“此‘虫’非彼虫”课程)
如本文开头所述,像蛇、蜥蜴这类平时不常见的动物出现在课堂上,孩子们一开始会非常害怕。
对此,李宗瑾认为从小培养孩子对于生物的科学认知是极其重要的:“每个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的,它都是地球的整个生态圈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每个动物都有它独特的美,只是有可能这种美是不被大众接受的。我们害怕蛇,这是正常的,蛇也害怕我们。我们不是要打破大家对它的恐惧,而是要打破大家对它的偏见。但不要一上来就认为它是邪恶阴毒的象征,就要伤害它。蛇其实是很温顺的,很少主动伤人。”
“我们讲爬行动物的时候,就以神话为切入,然后介绍蛇,问孩子们,在你们的想象中蛇是什么样?蛇应该怎样行走?等我们把活体蛇拿出来的时候,孩子们肯定会尖叫,我们开始引导孩子们怎样科学地观察它,然后引导孩子们科学接触它。”
(注:李宗瑾回母校博览园讲解时带上了小动物)
至于如何将这套自然科学课程体系流程化地梳理出来,团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是科研团队出身,刚开始也没有教学经验。之后招了师范专业的伙伴,开始系统化地做教案和课件,前前后后差不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每有新老师入校,需经过校方的试课方可正式带课。
与孩子们的互动与答疑,甚至延伸到课堂外。“每年4月到10月,他们在野外见到好玩的花鸟鱼虫,都会拍张照片在群里来问。”
关于考核,则是由团队跟学校共同协商出具体的考核方式,以检验团队的授课质量。包括给学生制作习题、考核笔记记录情况等。
(注:自然科学课堂上的孩子们)
“双减”前后,团队做进校服务是否有变化,李宗瑾表示:“之前我们就是长期稳定合作的学校有五个。但是在‘双减’刚出台那阵,当时鼓励的是音乐、美术、体育的三个方向,我们自然科学课,因为当时还结合了一部分自然课本内容(此前,学校是希望结合课本内容更深入讲解生物知识,比如候鸟为什么会迁徙、它怎样去导航、会不会导航失误等),所以当时就从学校里退出了。但现在比较明晰了。”
是否也有其他人在做类似进校自然科普的事,李宗瑾表示,“可能比较少。因为深入学昆虫学至少要读研读博,才能去研究所、生物科技类公司做科研,要么就直接转行。真正学这个、继续做这个的人太少了。”
这也是每每听到一些孩子说“长大了也想成为动物学家”后,李宗瑾千般情绪涌上心头的原因:“我一般是劝大家谨慎选择。你要确认是否喜欢这个方向。如果你只是一般般的喜欢,没有做好成为一个科研人员的准备,如果你面临生存问题,那建议你去选一个适合好好就业的专业。它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兴趣爱好。等你觉得这个真的是你想一生从事的工作时,再选择。”
(注:课堂活体展示观察)
03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一直做下去”
创业以来,几乎每隔两个月,李宗瑾脑海里就蹦出要撂挑子不干的念头。
令他最忧虑的是疫情。
创业本就前路未卜。但疫情之下,一切的不确定性都更为强烈:团队的进校业务、户外研学业务(与旅行社、机构合作,推出户外研学产品,并负责执行)都受疫情影响较大。
另一个让他头疼的是团队管理。
尽管他是90后,尽管这只是一个7人规模的小团队,但他仍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要论做产品,我们团队完全能做出来。但是我以往没有从商的经验,家里也没有经商传统,所以在管理这方面可能有一定的欠缺。管00后,那简直是要掉头发、甚至要谢顶的事情。他们这一代,家里也不差钱儿,管他们就跟在服务他们一样。”
李宗瑾说,最早的一批员工由于是母校的学弟学妹们,彼此很早就熟识,在专业性、执行力方面,团队的默契度很高。2020年初的疫情打破了这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停工数月,团队离散。
疫情有所缓解后,李宗瑾忙着新聘、培训新人。为了补上管理这一课,他甚至还报了一个商学院课程。
不过,他显然并没有学以致用。“必须承认,商学院的老师们讲得非常好,但是讲得太高太大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到十人的小团队来说,我如果用那样的一套公司管理方法去设制度管理团队,我觉得团队成员可能都要离职了。”
(注:城市周边动植物观察课)
就这样,带着每两个月就要摇摆一次的心态,李宗瑾动摇着,也坚定着,接纳着创业的甘苦,走到今天。
“团队目前实现整体盈亏平衡了吗?”
“严格意义上,倒也不算是亏的。西安疫情那阵子,我基本上把家底掏出来又投到公司里,相当于创业得来的,一并还回去。”
“那你还会一直坚持做下去吗?”
“当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一直做下去。”
他回答得干脆,能做就乐意继续做。“每每在野外,孩子随便指一个虫,我们基本都能认识,这才是我们团队核心价值的体现。我觉得教书育人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另外,根据政策导向,我觉得它也是有价值的。”
(注:城市周边动植物观察课)
后记:
“在走近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场景?”
“看到野生大熊猫、看到羚牛、被野猪追、被蚂蟥咬、被蚊子咬、被牛虻咬、被蜂咬、被蜱虫咬……各种被咬。”
“然后呢?”
“乐在其中。”
END
本文作者:徐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