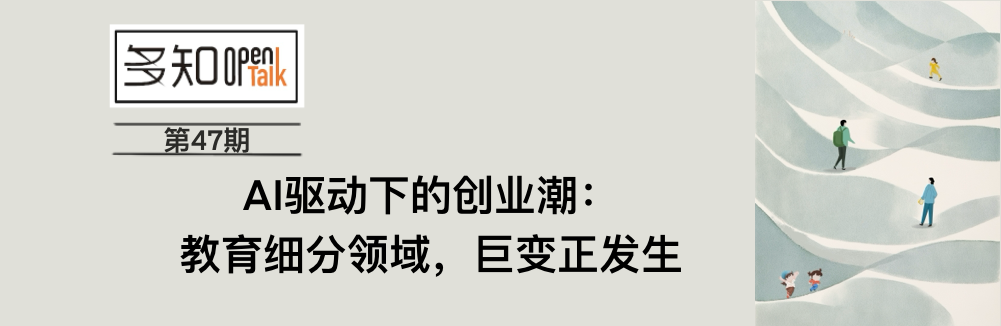如果孩子中途就跑不动了,赢在起跑线又有什么意义?
来源|一席
作者|一席YiXi
真实生长
2022.04.23 北京
大家好,我叫张琳,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我的作品《真实生长》在今年上线播出了,它讲述了十年前的三个孩子在一场教育改革中是如何成长的。
01
一场教育改革的展开
2012年八月,我大学毕业,走入社会。几乎是在同月,一群关注教育的媒体人在北京十一学校看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幕:
学校里取消了班级,取消了班主任,每个学生要自主选择导师,自主选择学习什么课程,每堂课换一个教室,实行走班制。全校有四千多个学生,就四千多张课表。
▲ 北京十一学校
有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是因为在前一年,十一学校被确立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因此,在2012年各项改革措施全面铺开。
当这些媒体人进入十一学校看到这一切之后,他们不满足于用一篇新闻报道或者一条电视专题去描绘所见到的一切,决定以纪录片的形式开启长期的跟踪拍摄。
他们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广泛拍摄学生和老师,最终,三位主人公跳到了镜头前——
周子其,从十一学校初中部直升进高中的文科生,喜欢历史、善于辩论、博览群书,关注现实问题。同时他也一直打游戏,是一个“非典型学霸”。
开学前,他就因为质疑军训的“游戏规则”,追着老师辩论。他引用洛克的话说,如果公众意志和人性相违背,我该遵从人性还是公众意志?老师说,公共意志。
这一幕恰巧被纪录片剧组拍了下来,成为了他在影片中的第一场戏。后来,周子其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关于军训如何不合理以及应该如何去改善的建议书,直接给了校长。
奇怪的是,他所有的建议都被采纳了,初中的军训取消了,高中的军训砍了两天。很显然,在十一学校的改革氛围里,周子其是一个如鱼得水的孩子。
李文婷,成长于山西阳高县,从怀柔郊区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十一学校的理科生。
作为一个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好学生”,刚刚进到开放的、自由的十一校园的时候,李文婷非常地不适应。在一群自信且成熟的北京孩子中间,她的羞涩和腼腆是显而易见的。
入学后,文婷很快怀念起了以前的生活。在以前的校园里面,一旦成绩退步,被老师揪着训一顿,训哭之后,成绩就又升上去了。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人管了,必须自己管自己。文婷很快就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之中,她压力很大。
陈楚乔,从其他初中推优至十一学校的理科生。本来她有机会直接保送自己的学校,可是她的爸爸说,你才十五岁,要什么保底,就直接去考十一。
这是一个理性、冷静又敏感的孩子,她一开始并不是我们的主角,但是在两三个月的沟通之后,我们发现楚乔是一个谈吐惊人的学生。这种谈吐并不是面向世界的侃侃而谈,而是对自我的冷静剖析。
她在高中的时候喜欢量子物理,喜欢艰深的科学,可是她却做不好一道高中物理题。她会说我不知道未来要靠什么吃饭,会坦诚地承认自己不喜欢承担责任。
她看了很多电影、小说,听了很多音乐,却焦虑于自己是一个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的人。
在镜头里,甚至在生活里,我们都很少能看到对自我有如此清晰认识的孩子。
02
三个孩子的成长
三个带着鲜明性格的十五岁高中生,在这样的校园里开始了他们的成长,同时也经历着成长带来的烦恼。
周子其,这个出场就自带高光的人,却在恋爱这件小事上遭遇了滑铁卢——他认为三个死党哪一点都不如自己,可是他们都有女朋友。
他是学校的辩论队队长,他带领的辩论社团蝉联了三年的北京市冠军。可是来到高二后,学业压力陡增,老师们开始侵占四点十五以后的社团活动时间。
辩论队没有办法训练了,他们头一次在对外的比赛中输掉了。周子其非常愤怒,他又写了一封叫《还“自主”以自主》的文章,在里面抨击学校的改革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明说要给学生自主的时间,却背地里安排了作业和考试。他把这封信发到了网上,捅到了校外,老师们也都很生气。
周子其遭遇的第三个烦恼,是跟爸妈之间关于专业选择的矛盾。
他一直喜欢历史,关注现实问题,却要时刻面对父母对自己的另一种期望——从事金融工作,未来“出任CEO,走上人生巅峰”。可是周子其并不喜欢,学习历史还是金融的纠结,一直伴随着他升入高三。
在高考前,他选择了妥协,他说毕竟爸妈是给自己上大学付账单的人。
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高考考“砸”了,砸到不能去爸妈希望他去的北大光华学院,“只能”去读历史。
李文婷选择了方习鹏老师做导师,这是个看起来传统、严厉、脾气大的老师。
▲ 李文婷的导师方习鹏老师
方老师会吐槽“学生的课表里面,体育课比我的物理课都多”,会当面跟年级主任争论,“让孩子们写规划是形式主义”,也会对着同学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
但是在方老师的指导下,李文婷在缓慢地进步。她在两个学期之后进到了前一百名,拿到了“双科飞跃奖”。
▲ 李文婷在“双科飞跃奖”领奖台
她也逐渐地有了一两个要好的朋友,大家一起养了一条金鱼。她还去参加了学校的泼水节,脸上有了笑容。
▲ 李文婷和好友一起养的金鱼
在高二的下学期,文婷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堂舞蹈课,要学习当时最流行的韩国女团舞。第一堂课,她的动作很不自然,也不太学得会,但是她会很认真地去跳。
最终在期末汇报的时候,她和同学们换上背心、短裤、高跟鞋,自信地展示青春的魅力。
尽管舞蹈动作还有一丝匆忙,但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个羞涩的女孩长大了。
楚乔的故事要从这间教室说起。
她选了一堂只有八个人的语文选修课,专门研读鲁迅的文章,本来以为只是了解一下文章的段落大意。
但开设这堂课的黄娟老师采用的是“抬杠式”教学法,她会不断追问一些非常浅显的问题,但需要孩子们有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语言回答。
▲ 陈楚乔在采访里谈到对黄娟老师课堂的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陈楚乔逐渐打开了自我。在一次课后讨论中她聊着聊着就盘腿坐上了桌子。
在这之前她从来不敢在课堂上这么做,这个动作一下子释放了她。
她开始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分享她喜欢的音乐——来自石家庄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歌。
她也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微型小说,并且在学校里面拿了奖,奖品是一整套《冰与火之歌》。
天空骤然明亮起来,
地平线上坦露出金红色的伤口,
可前因后果还没来得及说清。
“来了,来了……”
他喃喃道,
身子急迫地朝前探去,恍惚间他伸出的双臂像燃起了萤火,收音机嘶鸣不绝。
在我眨眼的瞬息之间,萤火蔓延视野,
他纵身跃下灯塔,落进了冰冷的海里。
-摘自《永夜的旅人》,陈楚乔
到了高二下学期,楚乔加入了微电影社。她和同学们想拍一部校园僵尸题材的微电影,预算要七千块。
七千块对孩子们来说是笔“巨款”,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以前的作品刻成碟拿去卖,结果只卖了三百块。
后来没有办法,他们开始向老师、团委、学生会等等寻求帮助,最后找到了校长。可是还没等展示预算清单,就被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校长说,钱是不会帮助你们的,就是要让你们经受挫折,让你们想办法,这才是锻炼你们。
最终楚乔和她的同学们被要求按照市场规则向校方进行一场答辩,讲清楚如何花钱,又如何回款,才获得了校方的投资。
最终在高三毕业的时候,他们拍摄的短片《极度恐慌》在学校上映了,不仅把钱赚了回来,还多赚了一点点。
03
从“教育突围”到“真实生长”
回到2012年,在刚刚选择这三个主角的时候,我们并不能预知他们未来将有怎样的人生,我们唯一确定的是,要记录这场教育改革对性格、志趣、背景都完全不同的孩子有怎样的影响。
因此,那时的影片名字叫《教育突围》,是想去呈现这场教育改革本身,跟现在的《真实生长》完全不一样。
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出了五集成片,直到那时候整个导演组才发现这个表达出了问题——如果仅仅去描绘一场改革是什么、怎么改,我们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没有任何立场去评判这场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
更何况随着教育改革的展开,像“选课走班”等制度在全国很多学校逐渐展开,这样的记录本身也不再新鲜了。
要如何让片子在更长远的未来里具有意义呢?整个团队都陷入了迷茫,发起人粟国祥老师个人投资的几百万预算渐渐花完了,团队成员也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最后只剩下了我和粟老师两个人。
对我而言,日复一日地观看孩子们的素材,他们已经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也逐渐地找到了我和他们更加个人化的联结。
我二十年前就是一个像文婷一样的乖乖女,一心只知道学习,只知道备战高考;我很快就知道了楚乔未来会成为我的同行,她拍电影,而我拍纪录片;我和周子其都在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里读书,我们会偶尔互相吐槽对方的学校,也对好学生会遇到的问题有深刻的共鸣。
于是,我留了下来,我决定转换视角来讲他们的故事。我想去呈现下一代人的自信与张扬,同时更想表达每一代人都会遭遇的迷茫和痛苦。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从职务和心态上都变成了片子的导演。很快,我们决定在影片制作和播出都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一方面启动对三个孩子大学生活的跟拍,另一方面开始去找投资和播出渠道。
从2018年底开始,我们去了广州,去了台湾,去了韩国釜山,去各种提案大会,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各种各样的人听。最后在广州纪录片节的帮助下,找到了腾讯视频来投资和播出,并且找到了周浩老师来当我们的监制。
我记得在2019年春天,广州纪录片节把几个潜力项目的导演和周浩老师聚在一块聊项目,我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场面试。我把预告片给周老师看了,跟他讲了三个孩子的故事,周老师全程面无表情。
周老师向我发问,用五个词形容一下周子其。我说的前四个都是显而易见的,才华横溢、博览群书、口才等等,周老师都没有什么反应。最后我想了想,说了第五个词,保守。
这个保守更多是指我看到子其这样的孩子对待金钱的态度。在2019年,类似于直播、知识付费、自媒体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一个拥有雄辩口才的年轻人会觉得自己以后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
这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会觉得他们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自信,他们有保守的一面。至此周老师终于听到了他想听的,他认为纪录片中的人物应该是复杂的、立体的,他看到了这个故事的丰富性,所以他同意来当我们的监制。
投资有了,播出平台有了,也有了更好的老师来帮助创作,按理说应该一帆风顺,我却在做到第三集的时候卡了壳。
整个片子有三个孩子和四个老师,一共七个主要角色在每一集都出现。教育本身又是个非常丰富的话题,想说的内容太多,片子臃肿不堪。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崩溃了,我停掉了手头所有的工作,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去讲什么。
最终是音乐拯救了我,突然有一天一小段非常完整的旋律来到了我的脑海里,有完整的四小节。我想说我可以拿它做什么呢?我就花了两天的时间完善了后四小节旋律,再花了两周的时间填上词。
写完歌词的那一刹那,我知道这就是故事梗概了,我终于知道要表达什么了。后来这一小段旋律和这一段词成为了片子的片头曲,由十一学校金帆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它和影片本身成为了我的主旨表达。
04
不为高考,赢得高考
今年二月份,片子上线了。三个主人公都来到了首映式的现场,这是他们十年后长大的样子。
楚乔跟我说,她觉得影片真实地捕捉了当时的空气,尽管她觉得有一种被公开处刑的羞耻感,但是她接受那就是真实的自己。
周子其说他已经淡忘了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淡忘了当时现场还有摄影机的存在,但他也承认当年的很多事情依然在他身上留有影子。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文婷看完首映跟我们道了歉。因为在高三阶段,她觉得耽误学习拒绝了拍摄。但我们其实觉得完全没有关系,也没有在片子中去呈现这一点。
实际上在影片播出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很多观众都发自肺腑地表达,“我就是李文婷”,她是引发了最多观众共鸣的人。
当然不止孩子们看到,也有更多人看到了片子,比如说周子其的死党之一,辩论赛手李睦麟。
他在看完第三集,看到周子其的那一封信在老师们中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之后,那一天晚上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最终他爬起来给当时的王春易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
在周子其发帖到网上声讨学校的事件中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个时候站在学生的角度的他,并不能看到事件的全貌。
当时尽管老师们很生气,但是没有任何老师向孩子们去表露过他们的不愉快,甚至王春易老师还在年底跟孩子们道了歉。
其实在这一场改革里面,十一学校的老师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负荷了远超于一般学校的工作量。他们有句口号叫“不为高考,赢得高考”,教育改革和高考成绩两手都要抓。王老师说,谁都要成绩,学生要,家长要,社会也要。
改革刚开始,最先接受的其实是学生们。没有人管了,大家都很开心。最难适应的是老师和家长们——孩子们要走班选课,书包要放在走廊柜子里,孩子们不小心把柜门钥匙丢了,家长就会着急;老师们不知道学生在四点十五之后去哪儿了,想给补补作业却根本找不到人,就有老师急得跑到年级主任面前哭,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教了。
那是一段被扰乱的时光,对于教育改革该如何具体执行,老师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一直都有争论和分歧存在,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拿到台面上讨论。
在之后的十年里,教育改革在全国很多学校推行,但被看见的太少了。十一学校的改革不是唯一的,但依然是艰难的,是所有人日拱一卒的努力成果。所以在我们看来,记录本身是有价值的。
05
我只是个“幸存者”
从拍摄到现在过去了十年,这不仅是三个主人公的真实生长,也是我和项目的“真实生长”。
对创始人粟老师来说,他没有想过拍一个纪录片会这么艰难,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而即便播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商业回报。
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做得最漫长、也最艰难的一个片子,但是我能坚持八年是因为我不仅在其中获得了成长,纪录片本身也成为了我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遇到这个项目之前,我是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人,通过高考从小地方来到了北京,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本质上我并不会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因为我成功地通过了它的考验,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幸存者”。
当看到片中孩子们和老师们的互动,看到他们所受的教育,我也有过非常羡慕甚至是嫉妒的时刻。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北京才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教育?
在一段素材中,现场导演直接抛出了这个问题——“你们才十五岁就如此成熟,是不是因为你们在北京?”学生愣了三秒后,给出了一个精妙的答案,“不是,当年毛主席在湖南的时候,他想得比我们更多”。
当看到这群孩子有这样的思辨能力之后,我开始透过他们的故事去反思我受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从四岁到十二岁,我学了八年钢琴,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录制过山东省钢琴考级的示范录像。
我还记得在1999年,学费已经涨到了五十块一小时,而妈妈的月工资才只有九十块。如果拿金钱去衡量,我在当年接受的绝对是一种“精英教育”。可是那样的音乐教育是面向考级和比赛的,没有人会关注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我小时候是个外表可爱的小女孩,却没有人看到我性格的本质——一个理性、严肃、善于处理多线程任务却不善于情感表达的人。所以,我弹得最好的是巴赫,却弹不好表演型的、面向比赛的曲子。
在传统的音乐教育里,没有人关注到我的性格和我在音乐上的喜好。他们依然是用那一把尺,来衡量我作为一个音乐学习者是不是成功,是不是优秀。
逐渐地我在学音乐的过程中越来越痛苦,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再加上学费又非常高昂,最后便放弃了。
回过头来看《真实生长》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每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就被鼓励去挖掘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以后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
如果在我当年学音乐的时候能够有人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孩子,能够有人跟我说,虽然你不适合做演奏,但是你可以去学作曲或者学指挥,或许我就不会放弃音乐。当然我还是非常感激妈妈把我送去学了钢琴,否则我不会写出我的片头曲。
所以每一代年轻人的成长都会经历焦虑和痛苦,这跟他身处什么样的时代无关,跟他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也无关。
06
你清华毕业的就干这个?
这批95后的孩子生长于一个物质充盈、信息爆炸的社会,他们在非常小的时候就见识到了更大的世界。可是当他们长大成人来到社会之后,却发现上升的通道似乎变窄了。他们有一腔热血、一身武艺,但现在或许只能做个普通人。
周子其在高中毕业之后去了北大学历史,可是半学期之后他就体会到那种学究式的历史教育不适合自己。
同时他也看到了很多更优秀的、更适合学历史的学霸是什么样的,他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差距。于是他辅修了经济双学位,并且决定出国。
他去了芝加哥大学学习公共政策,这是一个用数理模型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专业,算是综合了他个人的历史理想和爸妈对他从事金融工作的期望。
出国半年之后就遇上了疫情,他上了一年半的网课就回国了。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去了学而思,两个月之后工作就丢了,他不得不再找了份工作。
对子其来说,高中毕业后的这七年是一个认识自己从学霸变成普通人的过程。
我非常能够理解周子其作为一个北大学生所承受的期待和压力,在我从事纪录片工作好几年后,我曾经被人当面说,你清华毕业的呀,你清华毕业的就干这个?
一个人想要去做什么会受到来自他人的价值评判,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一种痛苦,所以我很理解周子其。
李文婷的故事没有那么曲折,她从十一学校毕业之后,考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习保险精算,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是北京孩子的大学。
她成绩很好,接着又被保送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是外地孩子的大学。
四年过去后,文婷发现自己比大学同学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她在做选择的时候不会那么痛苦。
文婷也一直跟她在县城的同学们保持着联系,坦白地讲,有些留在县城读书的同学们高考成绩是更好的,也去到了更好的大学。
可是很多人在一进到大学之后就丧失了奋斗的动力,或者说随便选了一个并不认识的专业,然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又或者随大溜儿考了研,到了研究生阶段又发现并不适合自己。
而这大部分的问题文婷在高中阶段都遇到了,也都尝试着去解决。她认识自己更早,也更清醒。对文婷来说,她接受自己现在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她愿意去过这样一种更为自洽的人生。
楚乔去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了四年电影,她在刚刚找到以影视作为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让我非常地动容。
我们问她为什么喜欢创作,她说无论多好的朋友或者家人最后都会离开你,只有作品不会。
她在创作中找到了非常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当她读完四年电影之后,她在毕业作品里致敬了刚刚逝去的姥爷。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楚乔回到了中国,开始一个剧组、一个剧组踏踏实实地去积攒经验。她跟我们说,她现在只能做场记,可是场记是除了导演和摄影指导之外,唯三可以坐在监视器前面的人,她可以学很多东西。
我们并不知道楚乔什么时候可以去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或者什么时候能够出名,但是我们知道她现在很快乐,并且在扎实地朝着她的梦想努力。
07
好学生的故事值得被讲述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个孩子都是好学生,那好学生的故事值得被讲述吗?
我在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后来才进入清影工作室开始纪录片创作。新闻专业给我带来了一个困惑,就是一个人要么特别好,要么特别坏,才会成为新闻人物。当一个人或者事件够不着这种新闻标准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不被看见的。
但是纪录片不一样,纪录片关注的是人本身,是人的生活和那些最琐屑的日常,这令我非常着迷。
《真实生长》的三位主人公无论从正面意义还是反面意义,都不是新闻人物。可是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焦虑和痛苦不值得被看见吗?
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记录他们的生活起码对我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坚持了八年。我相信能够打动我的影像,也能够打动更多人。
从一个好学生的视角出发,我看到了太多的人早早放弃了奋斗的动力。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可是如果孩子来到中途就因为太累而放弃了奔跑,赢在起跑线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十一学校,孩子们在高一高二享受到了相对自由的环境,但到了高三一切就像回到了解放前,课桌又摆回了原来的样子,老师讲课的方式、考试的频率,都回到了传统的模式里。对周子其这样的孩子来说,他们当然有一种乌托邦幻灭的感觉。
我前一阵还听说了这样一件小事,西南地区一所也有条件实行教育改革的学校,老师们会在高一高二到十一学校考察,到了高三,老师们又集体去衡水中学考察。
大人们的思维变化是很快的,可是孩子们不一定。当被逼到了最坏的份上,他们最容易做出的选择就是躺平。周子其当年是被寄予厚望要去争取北京市文科状元的人,可是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周子其会说,每天一睁眼就像欠了别人钱一样,他很不开心。
在高考之前,老师们围绕周子其的这种问题和他的职业选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时任学校战略顾问的李茂老师直白地讲:“像周子其这样的孩子,批判能力一点都不缺,他为什么没有激情,他是找不到如何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
周子其在高三阶段已经有一点点跑不动了,这让所有的老师都非常地焦虑。老师们不是焦虑他能不能考上北大,毕竟对一个在高二做二模题就能考全校第一的学生来说,考上北大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丧失对世界的热情、浪费掉自己的才华,这才是老师们最担心的事儿。
李茂老师接着说,如果十一学校的老师没有一点社会情怀,教得再好也无非是在为一些中产阶级的后代提供升学服务,这样的教育是可悲的。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四集一共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并不能解决这样宏大的社会问题,但是我可以用手里的镜头去提出一个问题。
漫长路如何独自前往?
我想这是对每一代年轻人都有意义的一个终极问题,我希望无论在何种教育体制下,孩子们在青春的年纪就可以去认识自己,去唤醒内心那份驱动自己不断前行的力量。
这力量足以支撑孩子们在漫长岁月中遇到挫折也不会放弃,并且可以不断摆正自己在更大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找到人生的意义。
片子播出后,有十一学校的学生跟我说,三年高中时光可能是他们现在的人生中最高光、最灿烂的时候。但是我想说,那样的灿烂其实从来没有消逝,它们只是变成了一抹非常微弱的火苗藏在了每个人心中。这个火苗会忽大忽小,但不会熄灭。
十年刚刚过去,三个主人公才刚刚步入社会,我们不能够以他们现在的境况去评判当年的教育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也希望所有来看《真实生长》的观众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能够藏有这样的一团火苗。
谢谢大家。
策划丨瓜西西
剪辑丨FH
图片丨均来自张琳和纪录片《真实生长》